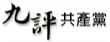每年清明、中元節前後,若是剛好返鄉,父母總會開車載我們到山寺掃墓,那裡供著阿嬤的塔位。隨著父母年紀漸長,開車的任務也落在兒女身上。今年造訪時適逢一場大雨,頗有「清明時節雨紛紛」之慨。我與父母站在阿嬤的塔位前,遺照上是熟悉的面容,只是怎麼也想不起兒時與她相處的點滴了。
母親在骨灰罈前喃喃祝禱,報告著兒女的近況,與祈求祖先庇佑的心願。儘管無法輕易憶起阿嬤的容顏,卻能深刻體會著這種代代相傳的血脈,確實的流動在我的身上。我想起前幾年與父母帶著阿公來掃墓時,他在靈堂中靜靜流下的淚水,那是兒女無從過問的回憶,牽連著心。而靈堂成排的塔位,隨著祭拜的人來去,想必也裝滿生者思念亡者的心情吧!
靈堂,像是隔離於物理時空之外的另一種時空,凝滯的氛圍停留在生命逝去的那一剎那。無論悲痛的眼淚、深沉的思念,都無法讓它流動半分,而傷逝不過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。
祭拜過後,我與父親在淅淅瀝瀝的雨中走過山寺的不二門,行經五百羅漢,踏上幾百級若川流瀑布的階梯,終於來到正殿。望著莊嚴且慈祥的佛像,彷彿亙古恆常的存在,度一切苦厄,內心忽感安慰。原來面對死亡的徬徨,與人生實難的慨嘆,正需要某些安定靈魂的力量。
佛殿外的師姐親切笑問:「從哪裡回來的?」我微感詫異,思索著「回來」這個詞彙的奧妙。師姐不問「從哪裡來」,而是「從哪裡回來」,也許正顯現了佛祖無限的慈悲與包容吧!彷彿在告訴人間汲汲營營的眾生,隨時都可以回來這裡。
離開正殿,行到地藏殿時,我敲了平安鐘。鐘響三聲,迴盪在雨中的山寺,鐘聲攜帶著虔誠心意,祝禱著身心康健、家庭平安,不過是最樸實無華的心願,在雨中漸漸擴散、曼延。
蘇打綠歌曲唱著:「我們都是一個人加上另一個人的長相,時間的牆從他們的手上到我們的肩膀。」當初跟著阿公掃墓的孩子,慢慢厚實的肩膀上承擔著時光的重量,眉宇間依稀越像父祖輩。而長大的我,忽然體會父親在阿公生前,每年堅持帶著年邁的他掃墓的深意,這無非是種孝心的展現,與父子間的羈絆。
靜謐的山寺,裝滿人類面對生死永恆的問答。於是生者會年年攜帶著深重的想念,來到這裡,隨著深山雨寺的鐘聲,一遍遍喚醒著那些曾經一起共度的,閃閃發光的回憶。◇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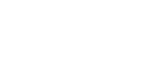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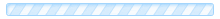 loading...
loading...